陕西省伊斯兰教协会
电话:029-87277685
传真:029-87277685
邮箱: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南院门机关小区综合2号楼5层

电话:029-87277685
传真:029-87277685
邮箱: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南院门机关小区综合2号楼5层
来源:《中国穆斯林》2020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20-08-06 10:05:27 访问人次:2814
学者档案
哈全安Ha Quanan

问:哈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穆斯林》杂志委托我所作的访谈。其实,这更是一次向您学习请教的机会。首先,能否简要介绍一下您的成长环境对您学术生涯的影响?
哈全安:谢谢你和《中国穆斯林》杂志对我的采访!我出生在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父亲哈雨田阿訇早年在东北多地清真寺求学,师从诸位先贤,曾与中国伊协原会长安士伟阿訇及原副秘书长马善义有同窗之谊。1942年在哈尔滨东寺挂幛,1948年起先后受聘于吉林市清真东寺和清真北寺主持教务。“文革”前多次当选为吉林市人大代表,“文革”结束后于1977-1987年任吉林省政协委员,1979-1987年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吉林省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和吉林市伊斯兰教协会会长,1990年后受聘于天津市多处清真寺。父亲勤奋好学,经训功底深厚,思想开明,加之性格耿直,常仗义直言,抨击有损教门的偏见拙识和狭隘之举。记得“文革”十年间,父亲被迫离开清真寺,闲居家中,仍恪守斋拜功修,信仰异常坚定而未见丝毫懈怠,白日操持家务,夜深人静时坚守拜功,晚年居家期间亦笔耕不辍,欲将自己毕生从教的心得体会传于后人。我本人深受家境影响,于懵懂之时耳濡目染,信仰已然植入心田,直至今日,虽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唯有内心的信仰不曾动摇。
问:您报考北京大学时选择历史学专业,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北京大学的学习生活对您产生了哪些影响?
哈全安:我的小学和中学是伴随着十年“文革”度过的,“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秋,我恰好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离开东北老家,走进了湖光塔影的燕园。从那时起,我便与历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年我的高考分数不低,即使在北京大学也有着相当大的专业选择空间。之所以选择报考世界史专业,其实自己的想法非常单纯,那就是少年时代目睹“文革”十年浩劫,厌倦繁杂的政治纷争,渴望远离喧嚣的现实,探索遥远国度的逝去岁月,在如烟的往事中寻觅内心的宁静。
我在北京大学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学习时光,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印象却是极其深刻的。那时的北京大学校园尚且处于城外,还很僻静,甚至有些冷清,校园的西侧和北侧满是稻田,周围鲜有商业网点,然而在校园里,声名显赫的学术大师却随处可见。北京大学深厚的学术积淀、宽松的学术环境和自由活跃的学术氛围是难以复制的,特别是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大学。每每回想起那段经历,心里总是充满了骄傲,常为自己的那段经历感到自豪。
二、阿拉伯中古史研究的拓荒者
问:北京大学毕业后,您选择回到吉林,后投师东北师范大学朱寰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人生选择?
哈全安:1983年秋,我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成为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的研究生,师从郭守田、朱寰和孙义学诸先生。那时的东北师范大学可谓大师云集,诸多学科位居国内一流,世界史研究领域尤其堪称东北师范大学的金字招牌,直至今日依然与北京大学齐名,并列高居国内世界史学科排名榜首。1988年秋,我再度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朱寰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入学伊始,朱寰先生对我说道,国内学者研究世界中古史大都热衷于西欧和东亚,尚无人问津阿拉伯地区,整个中东的中古史研究处于空白状态。先生考虑到我的身世背景,建议我以阿拉伯中古史作为未来的研究方向,我尽管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亦深知在学界空白领域拓荒之艰辛,却没有表现出半分犹豫而欣然接受。记得2019年12月在东北师范大学参加朱寰先生历史学终身成就奖的颁奖座谈会,谈起我与朱寰先生的师生情,我说自己是穆斯林,素以顺从作为准则,信仰方面顺从真主,学业方面顺从导师,先生吩咐我的研究方向,对我而言唯有顺从,别无选择。从那时起,我开始步入研究中东史的学术道路,研究方向再未有过丝毫的动摇。
入学之初,我没有按照正常程序在东北师范大学选修既定功课,而是只身前往地处北京西郊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由时任阿拉伯语系主任归运昌教授介绍,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期间,在归运昌教授的热情引荐下,我有幸结识了已过耄耋之年的学界泰斗纳忠先生,纳忠先生念及与我是教胞,加之曾与我父同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对我关怀备至。纳忠先生学识极其渊博,待人诚恳谦和。与纳忠先生数次长谈,既涉猎学术,亦交流信仰,尽数家事国事天下事,受益匪浅。1990年底经朱寰先生推荐,由教育部公派赴伊朗德黑兰大学进修。那时教育部公派留学名额甚少,持外交部发的因公护照,享受公务待遇,规格不低,实为万千学子心向神往的殊荣。出国期间,常心存感激而无以为报,遂发愤读书。在朱寰先生的悉心栽培下,我于1991年底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取得博士学位。
问:20世纪末,您在阿拉伯史的研究上已取得了丰硕成果。除了在权威的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外,还先后出版了《古典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封建形态研究》两本著作。这两本书,是您早期阿拉伯史研究的“姊妹篇”。两书将古代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和社会形态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地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凝聚着您博士毕业后10年间研究阿拉伯史的心血,具有拓荒和奠基性的学术意义。请您谈谈撰写这两本书的缘起和初衷?
哈全安:我在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的最初十年间,继续从事阿拉伯中古史的研究,关注的重点是早期伊斯兰时代即先知穆罕默德和麦地那哈里发的时代,就伊斯兰文明的起源、麦地那国家的形成、哈里发国家的变迁以及中古时代的土地关系和社会性质诸问题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算是在中东史研究上崭露头角。1996年初,我离开了学习工作十一年的东北师范大学,调入南开大学任教。大约在1998年初,我意外地收到了首都师范大学原校长齐世荣先生的来信。齐先生在信中邀我写一本关于阿拉伯历史方面的书,作为他主编的《精粹世界史》系列丛书的一种,并且叮嘱我务必遵循深入浅出的原则,先生的原话是“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表达深奥的学术内容”。于是,我倾尽全力,将此前近十年间所学写进书中,时间跨度上限为610年,下限为1258年,因多有学者将此间称作伊斯兰史的古典时代,该书故而名曰《古典伊斯兰世界》,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是为我从事学术以来第一部独立撰写的著作。
《阿拉伯封建形态研究》是我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阿拉伯封建形态研究”的结项成果,也是我独立撰写的第二部著作。长期以来,国内学者研究封建主义,主要仅仅着眼于东亚和西欧或者以亚欧大陆东端的中国与西端的英国作为典型案例,时而做东西方封建主义比较,时而做中英封建社会比较,至于亚欧大陆中央地带的阿拉伯封建主义,鲜有问津者。该书以有限的篇幅将阿拉伯封建主义置于亚欧大陆中古时代的宏观背景下,参照东亚和西欧之封建主义的种种现象,从动态角度考察阿拉伯封建主义的起源和演变轨迹,从静态角度探寻亚欧大陆封建主义的共性和阿拉伯封建主义的特质,着重论述伊斯兰教诞生后阿拉伯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诸多层面的历史运动,归纳阿拉伯封建主义的基本要素,曾被学界誉为国内阿拉伯中古史研究的扛鼎之作之一。
三、独标一格的中东现代化研究
问:在出版这两本史学著作后,您即转入到了中东的现代化研究。2001年,您在《历史研究》发表《从白色革命到伊斯兰革命:伊朗现代化的历史轨迹》一文,就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对伊朗现代化的历史作用给予了积极评价。您的相关认知与当时国内研究现代化的一些代表性观点不太一致。我们认为,这是您敢于质疑和挑战学术权威的勇气与魄力。2006年,您的《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一书面世,标志着您学术研究的转型。能否简要介绍下您从阿拉伯中古史转向现代化研究的缘起和相关考虑?
哈全安:记得博士毕业后不久,曾有前辈学者建议我拓宽视野,打通整个伊斯兰时代的中东历史,长时段地梳理伊斯兰教诞生以来的演变脉络。然而,我那时毕竟刚刚走进中东研究的学术殿堂,不仅是后学,更是初学,只能选择中古时代的少许问题,零敲碎打,至于打通中古与近现代的界限尚且有心无力。20世纪末,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成为国内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众多学者的目光转向探索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模式。此间常有国内学者附庸风雅,盲目追随西方观点,崇尚现代化进程之西方模式的经典地位,进而依据西化模式作为评判中东地区之现代化进程的尺度和准绳。相关论调充斥于学界,甚至成为风行一时的主流观点,而我对此不以为然,欲发出不同的声音,遂开始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倾尽全力考察中东地区的现代化道路。
比如,当时国内研究中东的学者对于所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多有关注,兴趣浓厚,却只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倡导回归早期伊斯兰传统而不知早期伊斯兰传统为何物。我便想以此为切入点做一点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我以后学身份去北京拜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杨灏城先生,杨先生是中东研究领域的前辈学者,素养极高,知我的研究重点是早期伊斯兰史,遂不耻下问,虚心交流,希望我能简要总结原教旨主义者推崇的早期伊斯兰时代有何显著特征。我思索片刻后向杨先生汇报道,相对的政治民主、社会公正和财产平等可以视作早期伊斯兰时代区别于其后诸多历史时期的显著特征。杨先生点头称是,夸赞我的回答解开了他长久以来的学术困惑,后学者的成就感随之浮上自己的心头。杨先生当年的肯定以及我自己的早年研究心得,也给我针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阐发自己的学术观点提供了信心。2001年,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从白色革命到伊斯兰革命:伊朗现代化的历史轨迹》一文,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写成的。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产生了不错的影响,据说许多高校的世界史专业将此文章作为学生必读的范文。从那以后,我更加集中精力全面思考现代化的理论构建,试图探寻中东现代化之于世界现代化的共性和特性问题。经过数年的努力,终于小有所成。2006年出版的《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的结项成果,以中东大国埃及、伊朗、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作为典型个案,剖析中东现代化背景下诸多层面的矛盾运动,探讨中东现代化的历史模式,是我研究中东现代化的第一本著作。
问:很多学者认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应当有着不同的模式。也有不少学者将西方现代化的某些特点拿来作为考察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标准。这其实还是“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和体现。虽然在人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确实揭示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某种趋势,但是后发展国家显然又不能完全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那么,如何来看待现代化?现代化的标准或指标应当如何确立?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又具有着哪些特点?
哈全安:这个问题很有意义。我自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长期在高校为本科生主讲基础课“世界上古中古史”,自研究领域由阿拉伯中古史转向中东现代化以后,学术视野随之拓宽,常从宏观角度审视世界历史,进而逐渐认识到,所谓世界历史即是人类不断走向解放的漫长过程,而人类之走向解放先后经历了两次深刻的转变抑或拐点:其一是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渡,其二是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前者的核心内涵在于原本从属于氏族部落和作为“整体的肢体”的个人逐渐摆脱血缘群体的束缚而成长为独立存在的社会成员,可谓“文明化”;后者的核心内涵在于独立存在的社会成员逐渐摆脱依附状态而走向自由,是为“现代化”。
在我看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终极目标无疑具有同一性,然而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却不尽相同,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历史的进步表现为否定与继承的双重过程,传统文明的特定背景赋予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以特定的历史印记。现代化并非等同于所谓的西化、欧洲化和美国化,亦非东方后发现代化国家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东地区的现代化作为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定内涵在于封建主义的衰落、传统秩序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传统的封建主义与新兴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运动贯穿中东现代化的进程。西方的冲击固然构成深刻影响中东现代化进程的外部因素,而伊斯兰传统文明的特定背景从根本上决定着中东现代化进程之区别于其它诸多地区现代化进程的特殊道路。
问:2016年,您出版了《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一书,通过选取埃及、伊朗和土耳其几个国家重点讨论了世俗政治和宗教政治在中东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特点和内在关联。部分学者认为,中东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即意味着世俗化,将宗教介入政治视为政治发展进程的逆向运动。能否就此阐述下您的相关观点?
哈全安:2016年出版的《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一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该书考察了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威权政治与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互动消长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深入挖掘中东现代化的特色与特性,进而阐述有别于国内外诸多学者的一己之见。在这部书中,我试图阐述如下的学术观点。
首先,常有国内学者追随西方观点,将目光聚焦于欧洲基督教世界中世纪的历史环境和近代早期之社会转型的历史实践,依据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历史经验,援引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现代化模式,将教俗二元的权力体系视作传统政治的典型特质,而将宗教领域的去权力化和政治领域的去宗教化,抑或教俗分离的所谓世俗化视作现代政治的特有形态,强调现代化与世俗化两者之间表现为同步性和必然性并具有普世的色彩。这种观点无疑具有西方中心论的明显政治色彩和历史痕迹。所谓世俗化并非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特有现象,自上而下的世俗化改革,缘起于西方的冲击,具有明显的西化色彩,长期伴随着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严格遵循宗教与政治分离原则的世俗化进程相比,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改革强调国家和政府对于教界的绝对控制,表现为宗教机构的官僚化和宗教意识形态的官方化,往往与威权政治的膨胀呈同步的状态,系官方强化对民众社会的控制进而完善威权政治的强力举措。中东伊斯兰世界世俗化改革的实质在于威权政治从世俗领域向宗教领域的延伸,与民主化进程背道而驰。
不惟如此,世俗政治并非现代社会的特有现象,而是普遍存在于不同的历史阶段,自古有之。宗教与政治的结合同样并非传统政治特有的历史模式,而宗教与政治的分离亦非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变的必要条件和必然过程。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无疑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却非存在根本的对立。传统世俗政治与传统宗教政治长期处于共生状态,皆强调人身依附和绝对顺从的传统政治原则。相比之下,现代世俗政治与现代宗教政治皆属现代文明的范畴,倡导自由民主的现代政治理念,与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具有同步性和内在逻辑联系。四、自成体系的中东史研究
问:2010年您推出110余万字的《中东史(610-2000)》(上、下编),实现了前辈学者对您的“打通整个伊斯兰时代的中东历史”的期待。由于对阿拉伯古典时期的历史和中东地区现代化研究都有着深湛的研究和独特的见解,也使得该书出版伊始便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2019年,《中东史》修订本被纳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能否介绍下《中东史》的研究构想、撰写修订以及出版后的学术反响等方面的情况?
哈全安:2010年由南开大学资助出版的两卷本《中东史610—2000》(110万字),是我自1988年读博起治学中东史二十年的阶段性成果。该书内容始于610年伊斯兰教诞生,截至世纪之交的2000年,原书名为《伊斯兰教诞生以来的中东史》,后来根据出版社的建议,改为《中东史610—2000》。鉴于当时国内世界史特别是中东史领域的大部头著作多为一人主编、团队执笔,鲜有一人独撰,于是暗下决心,欲凭一己之力完成百万字的长篇之作。该书的写作初衷是,不追随他人的观点,不重复他人的劳动,不居于他人已有的学术水准之下而力争实现学术超越。又见国内学者所著中东史专业书籍鲜有引文注释,遂欲另辟蹊径,力争做到有引必注,悉数列举书中引用的中阿英三种语言的文献资料逾四百种,页下注释逾四千条。《中东史610—2000》出版后,相继引起媒体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光明日报》刊载书介,将该书誉为“国内首部中东地区通史……填补国内中东史研究方面的空白”。其后,《华商报》曾经以整版的篇幅刊出专访。2011年,该书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2016年,在天津人民出版社责编任洁女士的精心策划下,两卷本《中东史》按照不同国别以八卷本的形式再度出版,翌年《北京晨报》以“我们应如何理解中东文明”和“中东文明是欧洲文明之母”为题刊出专访。在2017年出版的《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2010-2014)中,该书位列世界史学科排行榜榜首。2018年,该书获日知世界史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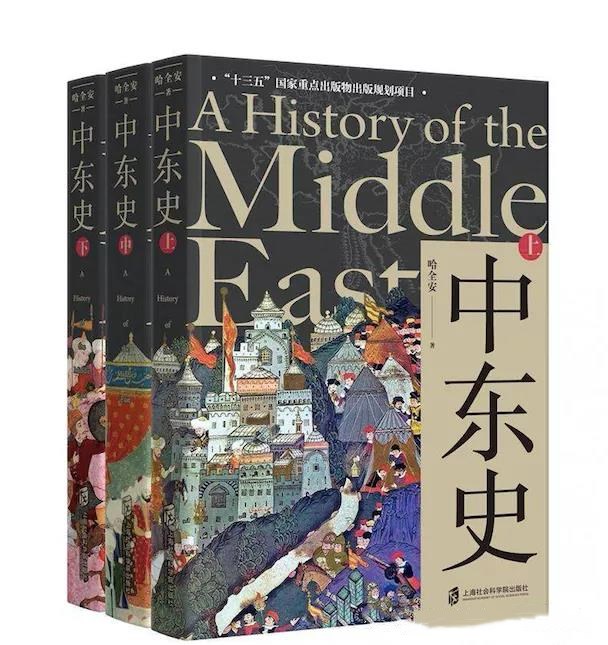
2019年,新的三卷本《中东史》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并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新的《中东史》157万字,时间下限截至2010年,内容较两卷本《中东史》增加近50%的篇幅,是我治学中东三十年的结晶之作。两部《中东史》的出版间隔近十年,贯穿始终的主旨是长时段和宏观视角下梳理伊斯兰教诞生以来中东历史的演变脉络,在理论层面总结和归纳伊斯兰传统文明之有别于其它诸多文明的若干特征,解读中东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轨迹,进而构建中东历史从伊斯兰文明的生成与固化到现代化背景下的震荡与新生之相对完整的认知体系,关于伊斯兰教的起源、阿拉伯封建形态、中东现代化理论、中东现代化进程的政治生态诸如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精英政治与民众政治、议会政治与街头政治、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以及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思想与实践等重大问题形成独到见解,自成一家之言。

问:在您的学术研究中,您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并自诩为“党外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对您的学术研究指导意义是什么?能否就相关研究谈谈您的治学心得?
哈全安:我从十七岁考入大学起,涉足学术领域,转眼已经过去了四十余年,似水流年间愈发深刻的体会是,宗教信仰与学术研究处于不同的层面,系意识形态的不同范畴。在我看来,宗教信仰无碍于学术研究,两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更非水火不容。我虽具有穆斯林的宗教背景,以伊斯兰教作为信仰的归宿和心灵的家园,却亦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受益匪浅。治学中东史三十余年,坚持遵循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作为自己的治学指南,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审视和分析伊斯兰教诞生以来中东历史上的种种现象,探因求果,自诩为“党外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形形色色的时尚思潮却不为所动。
强调社会形态的转换更替以及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基石,也是我治中东史三十余年长期遵循的学术准则。伊斯兰教脱胎于公元六世纪到七世纪初所谓蒙昧时代阿拉伯社会的矛盾运动,植根于原始社会濒临解体的社会环境,先知时代伊斯兰教的诞生顺应历史潮流,标志着阿拉伯半岛告别原始社会的野蛮状态进而步入文明时代的深刻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阿拉伯人的历史由此进入封建社会,直至1800年前后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逐渐启动现代化进程,转化为资本主义社会。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云,封建主义的解体使资本主义的要素得到解放。就中东伊斯兰世界而言,新旧社会元素的并存、转换和消长贯穿现代化进程,中东现代化的历史内涵乃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常有学者从唯心史观、意识形态决定论和文明冲突论的视角解读中东的地缘政治现象,强调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乃是天敌,认为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信仰差异是导致所谓文明冲突的根源,而当今中东的丛生乱象多系穆斯林内部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教派冲突所致。国内外专家言中东乱局必言教派冲突,强调教派分布与地缘政治格局之间的必然联系,似乎已成常态论调,实则不然。回顾历史便会发现,在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统治时代的中东,在蒂玛尔制度和米勒特制度的法理框架下,穆斯林与基督徒和睦相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亦相安无事,至于宗教迫害和教派仇杀只是偶发的特例,存在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并非常态化的普遍现象。众所周知,存在决定意识,而非意识决定存在;现实社会的矛盾冲突,根源于物质利益的争夺,而绝非根源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宗教信仰的差异,是为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将形而下层面之形形色色的矛盾冲突归因于形而上层面的信仰差异和教派对立,与客观事实和历史真相相去甚远,可不攻自破。在伊斯兰世界内部,就逊尼派与什叶派而言,两者之间的分歧和对立缘起于哈里发的权位归属,而哈里发时代早已成为过眼烟云,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复兴党曾经是“肥沃的新月地带”最具影响力的阿拉伯人政党,而来自逊尼派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与来自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却系同党,堪称复兴党双雄。1963-1967年,也门爆发内战,沙特阿拉伯支持也门国内的君主派作为代理人。也门的君主派实则来自什叶派分支栽德派,权力角逐跨越教派界限成为不争的事实。进入新世纪后,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两国关系不断恶化,海湾地区形成两虎相争的地缘政治态势,两国交恶的实质绝非源于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教派对立,而是在于后萨达姆时代海湾霸主地位的争夺。
通常认为,宗教改革是基督教世界的特有现象,基督教通过宗教改革而由传统的意识形态转变为适应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至于伊斯兰教则未曾经历过宗教改革,系传统范畴的保守意识形态,是制约伊斯兰世界社会进步的负面因素,所谓“宗教对抗国家”则是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唯物史观明确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意识的相应变化。诸多宗教尽管根源于特定的社会现实,却非处于一成不变的静止状态,而是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经历着沧海桑田的变化。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伊斯兰教根源于公元7世纪初阿拉伯半岛从野蛮向文明过渡的特定历史环境,无疑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改造阿拉伯社会的重要理论武器。在中世纪的漫长历史时期,伊斯兰教作为官方学说趋于保守和僵化,逐渐演变为具有浓厚传统色彩和捍卫封建秩序的思想理论。然而,伊斯兰教并非孤立存在和静止不变的意识形态;现代化进程中客观物质环境的剧烈变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伊斯兰教作为意识形态的相应变化。随着新旧经济秩序的更替和新旧社会势力的此消彼长,伊斯兰教经历了深刻的裂变过程,进而形成新旧宗教理念的尖锐对立。自19世纪以来,伊斯兰世界之宗教理念的变革,从文化层面延伸到政治层面,从精英层面延伸到大众层面,其历史路径与基督教世界的宗教改革相比可谓异曲同工。
以唯物史观审视中东历史,便会发现,政治环境、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特定的政治环境塑造相应的政治思想,进而决定相应的政治实践,抑或统治模式决定反抗模式,高压的政治环境催生出极端政治思想和激进政治运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则为温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提供了必要的沃土。在巴列维国王统治下的伊朗,世俗威权政治极度膨胀,世俗政治反对派缺乏必要的立足之处,宗教几乎是民众反抗的仅存空间,宗教的狂热则是民众宣泄不满和寄托希望的首要形式。巴列维王朝之自上而下的高压统治,导致伊朗现代伊斯兰主义之自下而上的激进政治倾向。阿里·沙里亚蒂和霍梅尼倡导的宗教政治主张,系巴列维国王当政期间世俗威权高压统治的逻辑结果。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社会基础是徘徊于政治舞台边缘的下层民众,支持者遍布城市乡村。赛义德·库特布崇尚政治暴力,强调“战斗的伊斯兰”作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可谓纳赛尔时代世俗威权政治膨胀的产物。后纳赛尔时代,埃及政治环境渐趋宽松,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立场随之渐趋温和,致力于政党政治和议会竞选,直至抛弃“无参与的政党政治”和“无民主的议会选举”,走上街头广场,成为“倒穆运动”最重要的幕后推手。土耳其自二战结束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之间的权力角逐并未表现为尖锐的对抗和激烈的冲突,尤其是没有形成否定现行政治体制和重建伊斯兰政体的激进政治纲领。政党政治的活跃、议会政治的完善和选举政治的成熟,决定了土耳其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温和色彩。
问:您还非常重视比较方法的应用,您在总结中东现代化特点时,将中东伊斯兰文明、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东方华夏文明进行比较。2018年,您在《光明日报》“理论版”发表了《比较文明视角下的欧洲与中东:同源性与异质性的历史考察》一文,系统考察了历史上欧洲和中东文明的联系及其近代不同历史际遇和走向。这篇文章应当是您研究中东现代化的后续成果。请您分享一下相关观点。
哈全安:我从1988年读博起,一直是以中东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心无旁骛,从未有过左顾右盼和东张西望的杂念。2018年,我调入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新的工作环境促使我开始思考欧洲与中东两大文明区域之间的关系,写成《比较文明视角下的欧洲与中东——同源性与异质化的历史考察》一文,刊载于《光明日报》史学版。以往常有学者夸大欧洲与中东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强调欧洲文明与中东文明的不同源流和各自形成的特质,我却不以为然,甚至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以我之见,欧洲与中东的人种构成具有明显的同源性,分布在欧洲和中东的诸多族群具有广义上的共同家园,相互之间的密切交往源远流长,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神学理念一脉相承,《古兰经》亦云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崇拜的原本是同一神明,承认历代先知及其传布的经典皆为真主颁降的启示,圣城耶路撒冷可谓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共同的信仰坐标,而欧洲与中东的异质化缘起于现代化进程启动后欧洲的崛起与中东的相对停滞。进入新世纪以来,中东局势剧烈动荡,诸多国家秩序失控,乱象丛生,政治暴力泛滥,家园毁于战火,背井离乡者不计其数。中东与欧洲在地理上一衣带水,就中东而言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欧洲,中东与欧洲在血统上同宗同族,信仰同源,尤其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历史落差,两者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环境和生活水准诸多方面差异甚大,相信中东难民没有理由不选择欧洲作为躲避战乱的避难所。中东难民如潮水般涌入欧洲,可谓同源异质的背景下两者之间相互交往的新形态。2019年11月,我应邀出席北京大学主办的高端国际学术论坛——北京论坛,曾经以此作为发言题目,从亚欧非大陆的地理坐标和人种分布讲到欧洲与中东之唇齿相依的密切交往,再从古代日耳曼人入侵罗马世界讲到当下中东难民涌入欧洲,娓娓道来,发言结束后,会场上反响强烈,尤其是与会的国外学者一反沉默的常态,纷纷竖起大拇指,对发言之独到的视角和缜密的分析表示赞许。
五、参政议政及治学体会
问:从2003年起,您连续四届被推荐为天津市政协委员,三届当选市政协常委。据说您在政协会上“敢言”“直谏”,您觉得作为一名学者,应当如何更好地参政议政,服务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社会经济建设?
哈全安:2003年,由南开大学推荐,我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进入天津市政协,此后连续四届担任天津市政协委员,三届当选天津市政协常委,两届兼任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我本是一介书生,长期蜗居于校园,鲜与外界交往,社会阅历少之又少,无党无派,在政治上无心进取,参政议政并非自己的长项,见身边其他政协委员踊跃建言献策,常有无地自容之感,汗颜至极。然而,自己深知作为政协委员绝非只是光鲜亮丽的政治荣誉,更是沉甸甸的社会责任,须不计个人得失,以平民情怀,反映社情民意,关注弱势群体,仗义直言,敢讲真话,尤其是敢于发表独立思考后的独到见解,履行民主监督的义务,坦诚相见,但求不负人民的期望,不负组织的信任。书生参政十七年,初心不改,虽在诸多方面表现平平,乏善可陈,甚至有滥竽充数之嫌,却未曾讲过半句虚言,更是未曾进过半句谗言,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既不跟风从众,更不肯行苟且之事,尚且聊以自慰,扪心自问,无愧书生良知。
问:最后一个问题。听说《中东史》中的第一章将以阿拉伯文在阿拉伯世界出版,这既反映出您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又体现出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日益增强的声音。作为一名著名学者,您却很少参加学术研讨会,而是钟情于斗室箪食、青灯孤寂的书斋生活。请您给青年学者分享一些您的治学体会。哈全安:我自幼深受家境熏染,在饮食禁忌上过于较真,外出用餐多有不便,故而深居简出,极少在学术场合抛头露面,离群索居。就学术交流而言,常被学界同仁视作另类,亦曾被媒体谬赞为“学术莽原上的独行者”。不仅如此,我在中东史领域艰难跋涉三十余年,既无团队,亦无平台,更无头衔,可谓彻头彻尾的三无人员,个中艰辛自不待言。以一己之力,成一家之言,独钓寒雪,独木成林,是我所追求的治学境界,未曾改变,亦无心改变。在我看来,学术交流固然重要,闭门造车断不可取,然而交流方式未必拘泥于特定的形式,更是不必随波逐流,既可取形而下之道,于豪华盛会欢聚一堂,推杯换盏间相互切磋;亦可取形而上之道,于陋室之中,寒窗旁青灯下,以文会友,闻其声读其文而不见其人。阿拉伯文版《先知穆罕默德时代》,选自拙作《中东史》,作为中阿文化交流项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项目,即将在阿联酋正式出版。欣慰之余,感慨良多,作为学术路上的独行者,回望来时路,一路独行,无妨学术交流。
(访谈者:马金生,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
本文原刊于《中国穆斯林》2020年第4期